“典籍英译人才培养的思考与实践——漫谈《中籍英译通论》”讲座回顾
10月13日,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潘文国应翻译系邀请回到母校,于文科楼424举行主题为“典籍英译人才培养的思考与实践——漫谈《中籍英译通论》”的讲座。讲座由翻译系系主任陶友兰主持,华东师范大学讲师陶健敏、复旦大学翻译系讲师强晓等专业教师参与。研究翻译的硕士、博士、访问学者30余人参与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陶友兰介绍了潘教授丰富的治学经历和深厚的学术成果。潘教授1962-1967年在复旦求学,他以刚刚出版的百万字新著《中籍英译通论》为主线,介绍了近年来自己在新时代中国典籍英译人才培养方面的思考与实践,着重讨论了中籍外译人才的知识结构以及典籍翻译教学等问题。
撰写《中籍英译通论》的缘由
讲座伊始,潘文国教授从威尔士大学汉学院教授《汉学英语》课程时的经历谈起,解释了《中籍英译通论》的写作原动力及素材来源。他认为,“不能找一个译本奉为经典就拿去学”,应当让学生学会评价,进行不同译本的比较,从中找到最好的翻译方法,创造更好的译本。“我们不是来学经典的,而是去找一个创造经典之路的”。在典籍翻译的过程中,特别是中国古典哲学的翻译,对中文的表述能力其实要求更高。
同时,在谈到《四书》《五经》译本时,潘教授认为,论理解准确、表达到位,还是理雅各的版本最值得肯定,因为在翻译过程中有学者王韬的帮助,并指出中英译者结合的合作模式是典籍英译的关键之一。其次,对于典籍翻译的评价方法,应该在多译本的比较中进行,不能确定所谓的权威性经典译本,并将经典译本作为教材使用,这样固化了典籍翻译的定义,因此,不能将典籍翻译的产出看作是静态的学习,而应看作动态比较中的互动性产出。潘文国教授还给大家详细描述了自己在汉学院授课时,怎样带领学生处理《隋书经籍志》等文本的经历。
《中籍英译通论》的特点
在介绍新著《中籍英译通论》时,潘文国教授着重介绍了第一章关于中国文化的问题,也就是“典籍翻译到底翻译什么”的问题。潘教授从“经史子集”的形成与发展出发,说明了文化史和治理学的内在联系,阐述了从源头探究中国文化体系的思路。他指出应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思考其对当今世界的贡献,由此向世界推广。潘教授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先推荐了国学初阶阅读书目,并结合“文章翻译学”对典籍翻译的未来发展,给出了自己的路线图。第二个特色是强调中西方学科建设的不同,他号召学界关注中国目录学对当代学科构建的启示;第三个特色是结合翻译理论和具体的翻译实例,荟萃东西方翻译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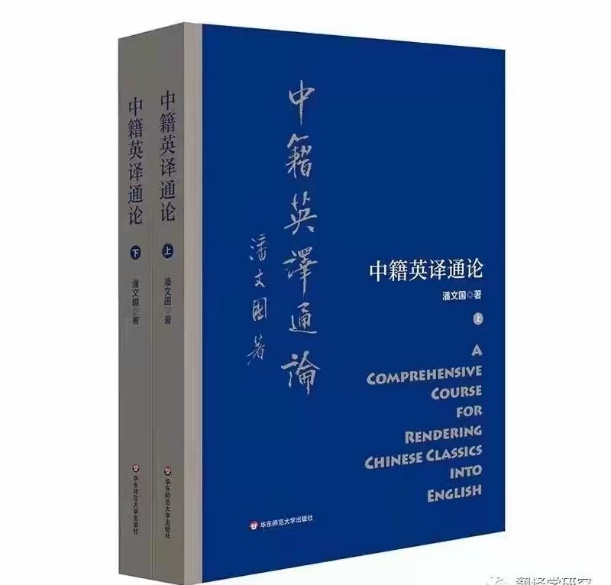

翻译史的发展观
在讨论翻译史时,潘文国教授强调了发展的观点,即不强调学者个人的全部成就,而是将重心放在每位学者对前人的继承和发展,着眼于为历史做出的贡献,由此明晰发展脉络。他认为,翻译史应是动态、发展的翻译史,而不是静态的史料史。
讲座结束后,陶健敏和强晓分享了在教授典籍英译和培养留学生方面的心得,并提出译者应当主动承担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责任。在场的师生讨论互动气氛热烈。



最后,陶友兰进行了总结,她认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迫切需要培养高端的汉译外人才,尤其是典籍英译人才,既要熟悉中国经典典籍,又要用英语读者理解的方式讲述中国文化的精髓。本次讲座老中青三代学人会聚一堂,“学而问之、聚而论之”,畅谈典籍英译人才培养,分享翻译学习方法,探讨典籍翻译研究之道。在场师生表示,作为年轻的翻译学子,不仅要提高双语水平,尤其是重视提高母语水平,还要具备全球视野,立足当下,从现实角度思考传统文化的传播问题,肩负起推广中国文化的重任。

潘文国教授在书上题字并赠予同学

精彩问答
Q. MTI在读硕士生朱维函:请问各位老师如何看待翻译和写作的关系?
潘文国:从文章翻译学的角度来说,翻译就是写文章,要用传统对待写文章的态度对待翻译。
强 晓:即使是忠实于原文的翻译,也有写作的成分。如果是在需要译写的情况下,首先要明确对原文忠实的程度,有充分的依据,才能译写。我们常说翻译是“戴着镣铐跳舞”,虽然过程中受到限制,但既然是跳舞,那姿势肯定要优美,所以本质上还是一种写作。
陶健敏:我想到了您提出的典籍翻译的“道”和“器”的观点,译者的创作空间毕竟有限,还是应遵循“信达雅”的“道”和“义体气”的“器”。
陶友兰:此外目的语的写作能力要非常强,比如严复和林纾,本身语言功底就非常深厚。建议大家回去看看潘老师关于文章翻译学的论文,能帮助大家理解如何做翻译,入门不要一上来就做埋头翻译,不懂道理容易走错方向。
学生感想摘录
陈烨儿:潘教授在探讨典籍英译的教学过程中,提到了相比于告诉学生以某一个固定译本为准,教师应该做的是和学生一起构建起评价体系,引导学生进行系统性地广泛比读,并形成自己的意见与译本。我不禁对这一“评价体系”产生好奇:此体系具体是如何架构的?其是否只是一个理想化的构想?这一体系是如何在形成相对稳定的评价准则和鼓励译者自主性、创造性之间谋求平衡的呢?这也是我在接下来阅读潘教授的著作时准备重点关注的问题。
胡笳韵:这次讲座对我最重要的启示是中国文化要“以中国的方式讲出来”,不能只追求一时的意趣、成效而失了根基。之前自己在翻译和研究的时候常常会很在意“可接受性”,不自觉地套用西方的概念,想来可能适得其反。另外,典籍英译离不开对中文本身的通透理解;正如老师所提到的,许多汉学家翻译中国典籍时也得益于中国人的帮助,我们作为母语者,更应该锻炼自己的中文文字能力,从辨识繁体、通读古文等开始。此外,“作为治理学的中国经典”、“发展的眼光看待翻译史”、“用诗歌表达译论”这些观点都颇显新奇,令我受益匪浅。
刘雨桐:对于中国典籍,尤其是《诗经》这样夹叙夹议、韵律工整的诗歌体裁应当如何翻译、直译还是意译好?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年初,我以《诗经》究竟该如何译为主题,选取了理雅各的1871 年译本(基本为放弃押韵的直译)和许渊冲的 2013 年译本(多为押韵的意译)中的一些例子,做了一个在线调查。有趣的是,国内大部分读者对许渊冲的译文打出了较高的分数,原因是其“贴近英文的表达习惯、有助于外国读者理解、手法较为生动形象”;外国友人则认为理雅各的直译有利于他们了解中国文化,而且为读者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而许译有过度阐释之嫌,且其表达方式并没有理译那么地道。所以,像许渊冲或埃兹拉·庞德那般在诗歌翻译中再创作是否真正地帮助了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我认为还有待探索。
张慧平:在这之前,我时常会觉得中华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各类书目汗牛充栋,学习典籍英译时也会觉得有些枯燥和无从下手。但这次讲座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先从最经典的文本读起,在理解原文内涵的基础上再谈英译或许是一种更为行之有效的学习和研究方法。
Copyright © 2021 bet365备用网址-bet365在线 版权所有 沪ICP备05013629号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
 学院地图
学院地图
 友情链接
友情链接



